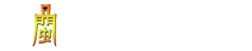村子里的居民基本上都被“养”了起来,每家每户都聘请一个保姆,保姆的工资每个月就有1800元左右。
经过半个世纪的接力移民,真正的曹朱村已经迁往美国。如今在美国的村民已经有三千多人,而还住在村子里的人已经低于1000人。
曹朱村的日渐衰败和中国的很多农村同步,不同的是,这里的凋敝不是因为贫穷,而是因为富有。人们怀着美国梦陆续离开这里,幸福指向的终点站是那个13小时时差的遥远城市———纽约。这个按捺不住强烈改变愿望的村庄是整个长乐市的缩影:村民不在纽约,就是在去纽约的路上。
曹朱村的记忆正在被迅速掏空。
村里的卫生员曹碧林今年做人口健康档案时发现,还住在村子里的人已经低于1000人。三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503。从明朝建村以来,这个村子人口少有地降到了千人以下。
当年青壮年纷纷离乡出国的踊跃场景如今已经不见。1980年代末的时候,人们不时能在村口看到声势浩大的青年们结伴同行,人们互相道别,场面像是斯巴达人告别前往温泉关的勇士。
曹朱村隶属福建省长乐市潭头镇管辖。历史上长乐曾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,即使在“片板不许入海”的时期,人们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操舟为业。从曹朱村到福州,城乡巴士只要一小时,但这儿离海更近,走到海边只需十五分钟。
1960年代,第一批曹朱人跳船登陆美国,当时只有三五人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,偷渡成了人们从现实中解脱的最好办法。
经过半个世纪的接力移民,真正的曹朱村已经迁往美国。如今在美国的村民已经有三千多人。
这里的村庄反而像是被遗忘在大洋此岸的飞地。即使在村口晒太阳的一溜婴儿车,里头躺的也基本上是美国公民———他们远在纽约的父母因为每天要繁忙工作13个小时,才不得不把孩子送回家托老人们喂养几年。空荡荡的曹朱村静卧在阳光下,现在和十年前并无不同,只是人更加稀少了。虚空笼罩在村子上空,人声和狗叫都显得乏力。在村委会门前的空地上,总能看见几十个晒太阳的老人———这很可能就是留在村子里一半以上的原住民———把一只手塞到另一只手的袖管里,用同样的姿势聊一整个上午,话题是地球上最繁华的城市纽约。
一整个早上人群里惟一一次发出轰动和声响,是65岁的曹典武夹着一只亲手打死的老鼠在人群面前走了一圈。他在美国打了16年工,在华人街脏乱的厨房里不知道打死过多少只老鼠。25岁的曹晓东曾经是短暂的瑙鲁国公民,他只去过那个国家一次。十几年里,他同样很少再回到曹朱村,大部分时间他和母亲生活在福州。
曹晓乐的表哥曹敏凡比他大一岁,现在也离开了村子去东莞管理一家工厂。他们小时候的同学都已经出国打工,有的在纽约的唐人街刷盘子,有的在送外卖,有的甚至到外州开起了餐馆。连曾经就读的曹朱村小学也因为招不到学生关闭了。本来表兄弟二人这时候也应该在美国,每次见面聊起这个事情都不免感慨。
不在纽约,就在去纽约的路上。
当地人在美国的一个俗语是“白天炉头,晚上枕头,周末律师楼”,“律师楼”说的就是非法移民在美国不得不苦苦寻求身份。
人们在福建沿海搭上一条渔船驶往公海,再换上一条大船开到东南亚的泰国、越南或者老挝,再从那里远涉重洋去往墨西哥,再从墨西哥边境狂奔翻过山脉,到达梦想中的美国。
曹朱村的日渐衰败和中国的很多农村同步,不同的是,这里的凋敝不是因为贫穷,而是因为富有。人们携带着海外汇来的滚滚财富陆续离开这里,去邻近的福州和长乐市区购房,过起了安逸的生活。而幸福指向的终点站是那个13小时时差的遥远城市———纽约。这个按捺不住强烈改变愿望的村庄是整个长乐市的缩影:村民不在纽约,就是在去纽约的路上。十多年前,曹敏凡的父亲在家中已经办起工厂,权衡再三之后,依然决定出国。在当时的村子里,出国有着类似于“进京当官”的极高荣耀。
他们顺利地和瑙鲁总理握上了手,并把微笑印在了相片上。笑容亲切而真诚,露出八颗牙,这很重要,尤其当护照放在入境检察官的面前时。
曹晓乐一家人以这种方式上路了。顺利的话,那一年他就能与将近十年未见的父亲见面。
他们入境新加坡没有遇到任何盘问,在那里成功地和一位美籍华人的导游会合。导游告诉他们,最关键的是第一个章盖上了,后面的入境旅游就好比累积信用,旅游的可信度大大提高,一切就好办多了。
一家人在新加坡享受了一个月的假日时光。那里干净的街道、规矩的行人都给曹晓乐留下了鲜明印象。除了6月底的一天,他们经过一个广场看到的新闻报道让人感到些许不安———在英国多佛尔港,海关官员发现一辆长途货车里闷死了58名偷渡者,其中的大多数人就来自福建。
这起死亡事件对于曹朱村乃至整个福建的移民潮影响深远,至今仍不时地被人在报刊上提起,从此以后大多数人抛弃了这种风险极高的“偷渡”方式,更多地采用了成本较高但相对安全的“旅游”。曹晓乐一家人暗自庆幸自己不需要那样“蛮干”,却完全没有料到这个事件的影响。
因为类似的死亡其实在村子里从未停歇。曹晓乐的一个亲戚在从墨西哥翻山进入美国时,被墨西哥军警开枪打死;另一个村民在途中反复被抓,最后藏身于粪车之中,进入美国时已被呛死。
死亡是源源不断移民过程中的惨烈代价,但这没能阻止人们出发的脚步。那些早年就移民美国的人在村子里总能留下令人向往的传说:绿卡、高收入、失业保险、低收入救济、免费医疗、免费教育……
移民美国对曹朱村民乃至整个潭头镇而言,意义如同成人礼,走出去意味着男子有拼劲、有前途。“实际上人们没有选择。”村委会的会计曹祥仁说。留在家里不仅仅是件没面子的事情,最为重要的是,村里的土地极少,种水田或蔬菜一年都只有几千块钱收入。即使留下来打工,每个月一两千块钱的工资也不能有尊严地生存。
多佛尔惨案在当时令很多国家入境管理严格起来,曹晓乐一家的“旅游”也终于在加拿大边境戛然而止。
入境检察官从母子殷切而紧张的眼神中产生了警觉,于是就在护照上盖了个鲜红夺目的拒绝章。这个章是一家人坏运气的开始,在返程途中,他们被一路拒绝入境,再次路过新加坡时,他们的瑙鲁护照甚至被没收。最后一家人不得不狼狈回国,在厦门被边防关起来盘问数日之后才放回家中。
这一趟环球旅游草草收场,一家人掏出了八十多万元人民币,最终却一无所获。
太平洋此岸的孤儿
一句形象的福州话在唐人街流传,说的是到美国打工之后,“三年一小'痴',七年一大'痴'。”“很多人连笑起来都显得僵硬了。”杨威说。他们也从海外汇回了大笔资金,修起了一座座美国国会般壮丽的礼堂。
表哥曹敏凡则一直在等待机会。由于当年父亲偷渡的“高超”技术和好运气,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需要贸然出击。但是移民局“假结婚”的认定同样令一家人陷入了困顿。他们决定在美国开庭上诉,争取扳回一局。
在地球的那一端,纽约的唐人街,表兄弟二人的父亲都在付出着同样的辛劳。从上午9点到晚上11点都是他们的工作时间。他们一个在前台当接线员,一个在当厨师,他们每天行走在垃圾和鱼腥味弥漫的街道。在电话里,两个父亲很少向家人提起工作的辛苦,但实际上通过村口的信息交流,老人们很容易了解到各家的情况。
在那里,思乡、身份和治安问题都是考验。
杨威是长乐市区移民到纽约的人,现在是几个中餐馆的老板。他见过很多来自长乐各个村庄的移民,“生活辛苦就像牛马一样”,很多人长期打工已经不苟言笑,只是终日发呆。他曾经聘请过潭头的一个厨师,总是一边炒菜一边自言自语,一会儿沉默一会儿大笑。